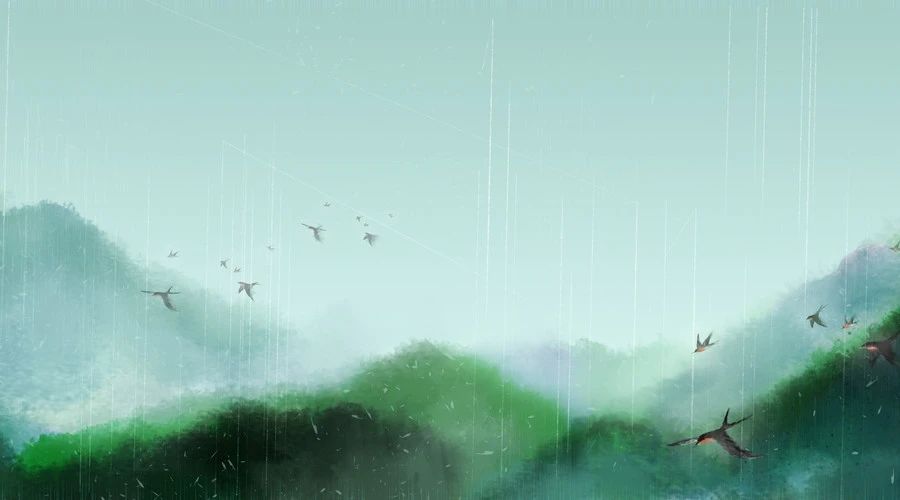大型文化节目《经典咏流传》用流行的音符唤醒经典诗词的生命力,掀起了全民“诗词热”。清代诗人袁枚的《苔》、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定风波》、元代画家王冕的《墨梅》等许多经典创作令人耳目一新,屡屡在朋友圈刷屏。
细腻的编曲结合多种演绎形式,让更多值得被记忆的好词佳句在时隔千百年之后流行起来、传承下去,越来越多的人恋上了诗词。 学诗词,喜欢诗词带来的美感,但诗与词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?唐诗和宋词作为古典诗歌中并峙的两大高峰,有怎样的差别?我们要表达的诗意,哪些适宜用诗来写,哪些适宜用词来写?我们来听听《向上吧诗词》总冠军、诗词世界专职讲师杨强谈谈他对诗和词的理解和认识。诗有诗的美,词有词的美,我们怎样去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来判定它?
以我们读宋词三百首为例,你获得的感受,是不是跟读唐诗不一样呢?
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夜饮东坡醒复醉,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,倚杖听江声。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。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句子的美质,更接近词的特质美。词最本质的美,就是宛转流丽,幽微曼妙。即使是一模一样的两句,在诗中可能反响一般,放到词里,便成为千古名句。看下面两个例子:仔细琢磨,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这几句,是不是很接近词的这种美?
总体来说,诗一般情况下可以言志,论道,通禅,说理,甚至调侃。诗的开阔可以表达很多社会生活,词的幽深适合表达细腻幽微的情绪和心境。
这种区别是在词体演进中,在其消费功能中逐渐积淀起来的体式美感。当然,后来词体光大,成为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诗歌体式,但这种本质的功能性的差别,仍然影响着词的美感样式。像辛弃疾的词,看起来很豪放,但它能不失词的特质美,历来评价极高。有很多豪放派的末流,做不到这点,写词失去了这种幽微曼妙、婉转含蓄的美,结果沦为叫嚣、直白宣泄,这种词就很糟糕了。由于词的写作对象和功能限制,它的表达是很狭窄的,不涉及更多的其他内容,但就是这狭窄的一点,却无限地深挖下去,把人的最本质的情感体验烘托出来。
情感在这里不受外在的道德、政治等等因素的限制,不必象在诗那样,要一板正经的去表达一种意义,而只是深微地去说这情感的体会,向一个纵深面,深到无限。这就是诗跟词的差别。
词关注的就是个体最敏感,最真切的情感体验,要把那心中无限缠结,无可名状的心绪,一点点地铺展开来。宋人为什么热衷写词,导致词的繁荣,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另一面,在朝堂上可以一本正经,在家里,在宴会上,在歌舞中,不妨展示人的另一面。词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美感的样式,比如婉约的基调,女性的视角和口吻,柔美的情感等等,都跟这种氛围相关。即使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词体成长的那个历史环境,但凝聚在词中的这些传统,仍时刻左右着现代人去读词和写词。举两个例子。杜甫写过《羌村三首》,第一首最后两句说:夜阑更秉烛,相对如梦寐:夜很深了,夫妻相对而坐,仿佛在梦中,都不敢相信两人相聚居然是真的。你读这句子,感觉很凝重,很深厚,很简练。可是晏几道写《鹧鸪天》的时候,借鉴这个思路,表达出来效果就不一样。今宵剩把银釭照,犹恐相逢是梦中:今夜里我举起银灯把你细看,还怕这次相逢又是在梦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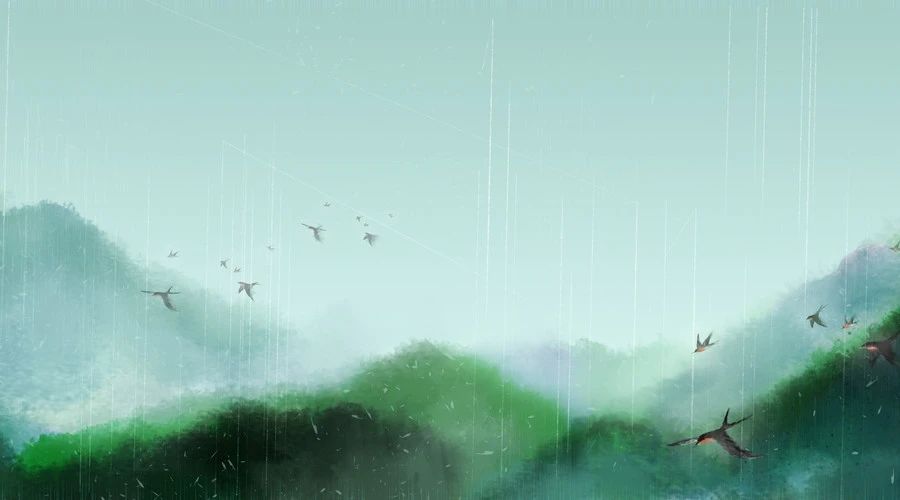
老杜的两句,放在诗中,是第一等的佳句;若是放在词中,就不符合词的这种宛转流丽,幽微曼妙的美,就不好了。佳丽地,南朝盛事谁记。山围故国绕清江,髻鬟对起。怒涛寂寞打孤城,风樯遥度天际。断崖树、犹倒倚,莫愁艇子曾系。空馀旧迹郁苍苍,雾沉半垒。夜深月过女墙来,伤心东望淮水。酒旗戏鼓甚处市?想依稀、王谢邻里,燕子不知何世,入寻常、巷陌人家,相对如说兴亡,斜阳里。从前在王谢大堂前筑巢的燕子,如今再来飞进平常百姓人家。你看,这样的句子很整饬,他用很简练的句子,抒发了无限的沧桑之感。想依稀、王谢邻里,燕子不知何世,入寻常、巷陌人家,相对如说兴亡,斜阳里。我猜想那破落里巷,大概是王谢两家旧庭院。燕子不知今为何世,飞入寻常百姓人家,斜阳里相对呢喃,似诉说古都兴衰。有人说,这句子很冗长。这样说的人,都是不懂词的人。没有人比周邦彦,更会把握词的特质美。你读刘禹锡的句子,它很紧凑。再读周邦彦的句子,很舒缓,句式长短变化,参差错落,起起伏伏,声情并茂,摇曳多姿。从诗的审美看,枯树、怪石都是美;从词的审美看,它更像一枝临水照影的梅花,在风中摇曳动荡,是一种脉脉含情,宛转跌宕的美。